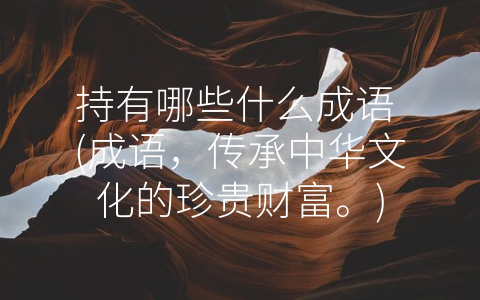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4期,原文标题《佛教造像:云冈、龙门、青州》,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佛教在两汉之际由精英阶层传入中国,却最终成为大众宗教,并在南北隋唐达到鼎盛。与此同时,作为佛教文化载体的中国佛教艺术,特别是佛教造像在南北朝时期大放异彩,诞生了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等艺术精品。公元6世纪,佛教又经由朝鲜进入日本,从而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佛教的发展和佛教艺术的产生。

记者/陈璐
东魏时期的背屏式佛三尊造像,是典型的北魏晚期秀骨清像式造像,且更能体现出北魏晚期的汉化造像风尚
菩萨头像,北齐,贴金彩绘,高33厘米
古印度佛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贵霜时代、笈多时代和波罗时代,而其中两个都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令该时期的中国佛教文化也随之得到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高峰。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中,师仿与创新同时并存,起源于印度的中国佛教石窟造像艺术,也因此有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
云冈石窟与犍陀罗文化
公元453年,高僧昙曜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一次相遇,改写了中国佛教的历史,也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存:云冈石窟。这是著名的“马识善人”的故事。据说昙曜从中山游历到当时北魏的都城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遇到文成帝出行的车队。文成帝并不认识这位高僧,但当昙曜为车队让出道路时,御马却张嘴衔住了昙曜的衣服不再前行。文成帝唤昙曜上前询问,发现这是位佛法高深的僧侣,拜他为国师,并命他开凿云冈石窟,这才有了云冈石窟的之一期工程,也就是如今的“昙曜五窟”。
这个故事被记载在《魏书释老志》上,同时也记录了开凿石窟时的情况:“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现在山西大同城西46公里的十里河北岸山崖上,东西连续约一公里的洞窟中,第16至20窟即是“昙曜五窟”,开凿于公元460至70年前后,以三世佛造像作为题材,每个石窟的中央都雕刻着高鼻深目、眉眼细长的巨大佛像,分别代表着北魏历史上的五位皇帝。
北魏建国前,鲜卑族拓跋部几乎与佛教无缘。西方佛教得以在中土大地扎根,离不开僧人法果提出“皇帝即为当今如来”的思想。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希望宣扬佛法的法果拜见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时,将他比作当世如来,并说“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佛教由此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推崇。
北魏永安三年的贾淑姿造佛三尊像,面部已经基本看不到北魏传统的秀骨清像特征
菩萨立像头像正面,东魏,贴金彩绘
云冈石窟第20窟的露天大佛,是云冈石窟的象征,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座佛像,代表的是北魏早期某一皇帝,传说是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由于洞窟的前壁已经崩塌,高13.75米的巨大佛像如今显露在外。这尊释迦坐像位于洞窟中央,左右是胁侍菩萨立像,然而右侧的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左侧这尊。主佛膝盖下的部位已看不太清,但胸部以上因为石质坚硬,保存完好。其造型古朴、气势宏伟,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剽悍强大,同时大佛面形丰圆,两耳垂肩,薄唇高鼻,袈裟右袒,带有有别于 *** 的特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李静杰教授告诉我,云冈石窟佛教造像强调写实表现,特别讲究人体的形体结构和比例关系,“这恰恰是汉化地区以前不受重视的方面,其根源在古希腊罗马,直接的动因就是犍陀罗文化的东传”。汉化地区,也就是敦煌以东,由中原王朝统治的地区一向不太注重写实的人体造型,只追求大体的形似。尽管也有秦始皇兵马俑的头部这样写实的雕塑艺术存在,但其身体都是用模范 *** 的,并且这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但在公元5世纪,因为犍陀罗文化的东传,中国汉文化地区的造型艺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犍陀罗为今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盆地周边地区,与阿富汗相邻,属于古代印度十六大国之一,因为地理单元上属于印度板块的西北部,又被称为西北印度。公元1世纪至公元5世纪,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盛极一时。因为犍陀罗地区地处东亚、中亚与印度次大陆的交通要道,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不同文化都曾深刻影响了当地佛教,形成了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
“犍陀罗文化是将古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和古印度佛教的教义相结合的一个产物。”李静杰解释道,“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带到这里,后来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人们将古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与印度的佛教教义结合起来,产生犍陀罗文化。犍陀罗文化兴起的时间也正好是佛教向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
《哈佛中国史》提到,是中亚的商人与从海上而来、到达江苏的贸易者率先将这种新的宗教带入中国。佛教被引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但之一个有关佛教的文字记录是在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使者口授《浮屠经》给西汉博士弟子,将佛教传入汉代。公元1世纪至3世纪,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正是犍陀罗文化的鼎盛时期。
然而实际上,虽然佛教传入汉文化地区的时间较早,但佛教的物质文化,即艺术等门类在早期还不太发达。“5世纪上半叶及以前,佛教造像是比较少的,主要流行金铜佛像,并且数量非常有限。”李静杰说,随着北魏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到5世纪下半叶及以降,石窟寺院的开凿带动了单体造像的发展,犍陀罗文化成批量地向汉化地区传播,促使汉化地区造型艺术很快趋于成熟。依照官方记录,到北魏末期,境内寺院多达13727座。
与此同时,犍陀罗文化在东传的过程中,不仅给佛教艺术带来了写实的造型,还带来了表现系统性佛教教义图像的 *** 。比如云冈石窟雕刻中多有描绘“燃灯佛授记”的故事,其故事主角是后来应身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儒童摩纳婆。最早有关燃灯佛授记的图像来自约公元1世纪左右的犍陀罗雕刻,通常通过“买花”、“献佛”、“布发掩泥”和“身升虚空”四个情节进行表现,这在云冈石窟中也同样如此。
不过,5世纪时的犍陀罗文化其实已经处于衰落期,但因为在北魏统一北方、再次打通陆路丝绸之路以前,中原北方长时间处于分裂的状态,导致繁荣期的犍陀罗文化并没有在同时期的汉化地区得到发展。犍陀罗文化在中印两地的传播时间便存在一个时间差。
这尊北齐菩萨立像尤能体现青州菩萨造像的高超技艺
“秀骨清像”造型风尚的流行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此为界,北魏佛教造像呈现出新的风貌,这正是从南朝流传过来的“秀骨清像”。
“秀骨清像”最初是一种绘画风格,表现为人物造型清癯消瘦,其创造者是南朝宋明帝时的皇家宫廷画师陆探微。陆探微是顾恺之的学生,而顾恺之的成名之作,正是绘于建康瓦官寺,拥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维摩诘像。陆探微在继承顾恺之风格的基础上,将这一风格发展成熟。唐代绘画理论家和美学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评论道:“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虽妙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这正是“秀骨清像”的来源。
“秀骨清像”反映的是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与哲理内涵,以消瘦的体形,配以魏晋文人随风飘动的宽袖衣袍,表现人物洒脱、超凡的神态与气度,正是当时流行的玄学清谈家所崇尚的道骨风韵。魏晋时期的佛教在面临影响力巨大的玄学思潮时,选择与玄学合流的方式,留下了清谈玄想的思想痕迹,为“秀骨清像”风格的佛教造像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时,与北魏对峙的是南朝的齐、梁,都十分重视佛教,但不同的是,当时南朝佛教艺术的发展与世家大族及文士、画师们的联系更为紧密。当时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实施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北魏皇室在向汉文化地区学习治国之策的同时,也极力推崇佛教的发展以促进民族融合。伴随着这一文化交流,南朝“秀骨清像”的塑画风格逐渐深入到北方,形成新的佛教造像风尚。
公元500年,魏宣武帝诏令在今天洛阳南郊12公里外的龙门开凿石像,这就是龙门石窟。在云冈石窟后期,佛像已经失去了昙曜五窟时期那种健壮、强悍的特点,人物形象更加清瘦、纤细,并且也不再是最初面带笑容、嘴角上扬的样貌,表情变得严肃,显得有些清瘦孤高。而另一边的龙门石窟,其初期佛像虽然五官还是鲜卑族高鼻梁、大嘴巴的特征,但脸形却变得狭长,身材也越发苗条挺拔,并且开始改穿“褒衣博带”式的汉族士大夫服装。
李静杰分析道:“5世纪下半叶云冈石窟人物造型特别注重的形体结构、比例关系、肌肉隆起等等方面,到6世纪上半叶完全颠倒过来,秀骨清像恰恰不重视人体的结构和形态,而是着力表现一种潇洒飘逸的气质精神。”
当“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中原风格一经形成,便以洛阳为中心向外传播,从洛阳地区,到云冈石窟、麦积山、炳灵寺,乃至凉州地区及敦煌莫高窟,莫不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影响。不过,尽管“秀骨清像”诞生于南朝,但因为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运动和战火,能够流传至今的南朝佛教造像作品所剩无几。除却历史文献中字里行间的描述外,还要从北方的造像中去寻找。
在南北朝时期的不同地区,具有“秀骨清像”特征的佛教造像,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例如甘肃炳灵寺的造像有如刀削般刚健挺拔,麦积山的造像线条柔和、清秀俊美,云冈、龙门的造像则仍然可以看到鲜卑民族的粗犷和强悍。但类似的是,它们都具有狭长的脸型和清瘦的身材,呈现出佛教进入中国本土化后对传统儒、道文化的吸收。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视觉中国供图)
来自青州的“东方维纳斯”
在山东青州博物馆,展示着一尊北魏至东魏年间的“彩绘石雕菩萨立像”,高187厘米,头戴贴金宝冠,面相圆润,虽然双臂残缺,但异常端庄秀美,因其特有的“青州微笑”,被誉为“东方维纳斯”。这是受到笈多文化影响的新风格的佛教造像。
“6世纪下半叶,或者更早些的6世纪中叶,印度笈多文化通过海路传到中国东南沿海地方,然后进入整个汉化地区。这时候,受笈多文化的影响,以前清瘦的审美又被一种新的风尚替代了。”李静杰解释说,“人物的造型变得非常圆润优美,除形体的结构外,还注重肌肤的形态,让人感到有血有肉,肌肤富有弹性。这时期的代表就是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当然这批造像也有一些其他风格,但这个风格最为典型,可以比较充分地看到印度笈多文化的影响。”
笈多王朝(320~6世纪中叶)时的中国,正处于东晋南朝(317~589年)与十六国北朝(304~581年)时期,这也是中国佛教艺术极为昌盛的时期。具有笈多文化特色的佛教造像,出现自公元4世纪后期,并在公元5世纪初期得到大力发展。其特点是面相静谧,两眼半睁半闭,呈冥想状,身体均衡自然,紧贴肌肉的轻薄袈裟覆盖着两肩到下肢,其中秣菟罗流派用隆起的线条表示衣褶,全身都覆盖着规律的平行线。这种衣服褶纹紧贴身体的表现风格在笈多王朝叫作“湿衣派”,在中国被称为“曹衣出水”,是北齐画家曹仲达创造的一种人物画的绘画风格。
“这时候我们看到佛陀的造型,不像以前那样双目圆睁,都是双目微睁,给人一种进入冥想的感觉,这种风格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这都属于笈多文化的贡献。”李静杰补充道。当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之后,笈多艺术对汉化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青州造像”与“曹衣出水”是典例的例证。实际上,在笈多王朝趋于全盛之际,犍陀罗已基本丧失了创作的活力。
思维菩萨像,北齐,贴金彩绘,高80厘米
尽管青州如今名声不显,但这里曾是古代中国的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中有“海岱惟青州”的记载,意思是从泰山到东海之间这片广袤的山川大地,现在的山东地区基本都属于古青州。作为东夷文化的发祥地,这里已经有7000年的发展史得到了考古验证,尤其是佛教文化,在青州有1700多年的历史传承。西晋时期,佛教在青州已经开始兴起,398年,在山东建立南燕政权的慕容德也对佛教十分虔诚尊崇。
青州地近南朝,又濒临东海,拥有通过南朝或直接与印度交流的便利条件,六朝以来,与南洋群岛、印度之间的海舶交通往来不辍。根据《佛国记》记载,东晋高僧法显曾前往天竺寻求戒律取经,历经14年后,于公元412年归国,曾亲眼目睹了笈多盛世。他本来准备从印度尼西亚搭船前往广州登陆,结果被大风吹偏了航线,从青州长广郡的崂山南岸登陆,比计划多走了20天。因为当地太守的挽留,法显又在此讲法一冬一暑,直到第二年秋才回到建康。“法显所处的时代,包括青州在内的汉文化地区的佛教已经比较发达了。但是青州的艺术是印度的笈多文化通过东南亚这边传过来,这是比较明确的。”李静杰强调。
从青州出土的实物来看,北魏晚期的青州佛像与北魏晚期北方地区的风格基本相同。到东魏时,虽然青州佛像仍带有北魏晚期的风格,面相长圆、身体修长,但岌多艺术对青州佛像的影响已经开始出现。这时期青州多数佛像皆以螺发为头饰,但此前北方地区的佛像较少出现螺发,而都是犍陀罗式的涡旋状发型或磨光发型,但其肉髻仍保持了北魏晚期高隆的特点。比如出土于北魏至东魏年代间的一座背屏式佛三尊造像,其整体风格为北魏典型的秀骨清像式样。主佛的面部较大,头部表面饰有螺纹,身着褒衣博带,但较为轻薄贴身,勾勒在消瘦修长的身体上。而左右两边的菩萨身体比例则较主佛更为和谐,但也充满清秀潇洒的风尚。
直到北齐时期,青州佛像才大量接受笈多艺术的影响,除薄衣叠褶外,北齐佛像大多形体流畅,薄衣下隐现紧实圆润的肌体轮廓。例如青州出土的一尊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肉髻低圆,螺发卷卷,面相丰圆,五官较为集中,双目微启,神情宁静。
“过去研究佛教文化的时候,有些人认为南北朝是隋唐佛教文化的一个前奏,或者是一个初步发展阶段。”李静杰指出,“但实际不是这样,南北朝隋代和唐朝应该是佛教文化并列的两个高峰,但从规模上讲,它比唐朝更大一些。”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宝丁翻拍/青州博物馆提供)
云冈龙门佛教造像 最新佛教造像福田